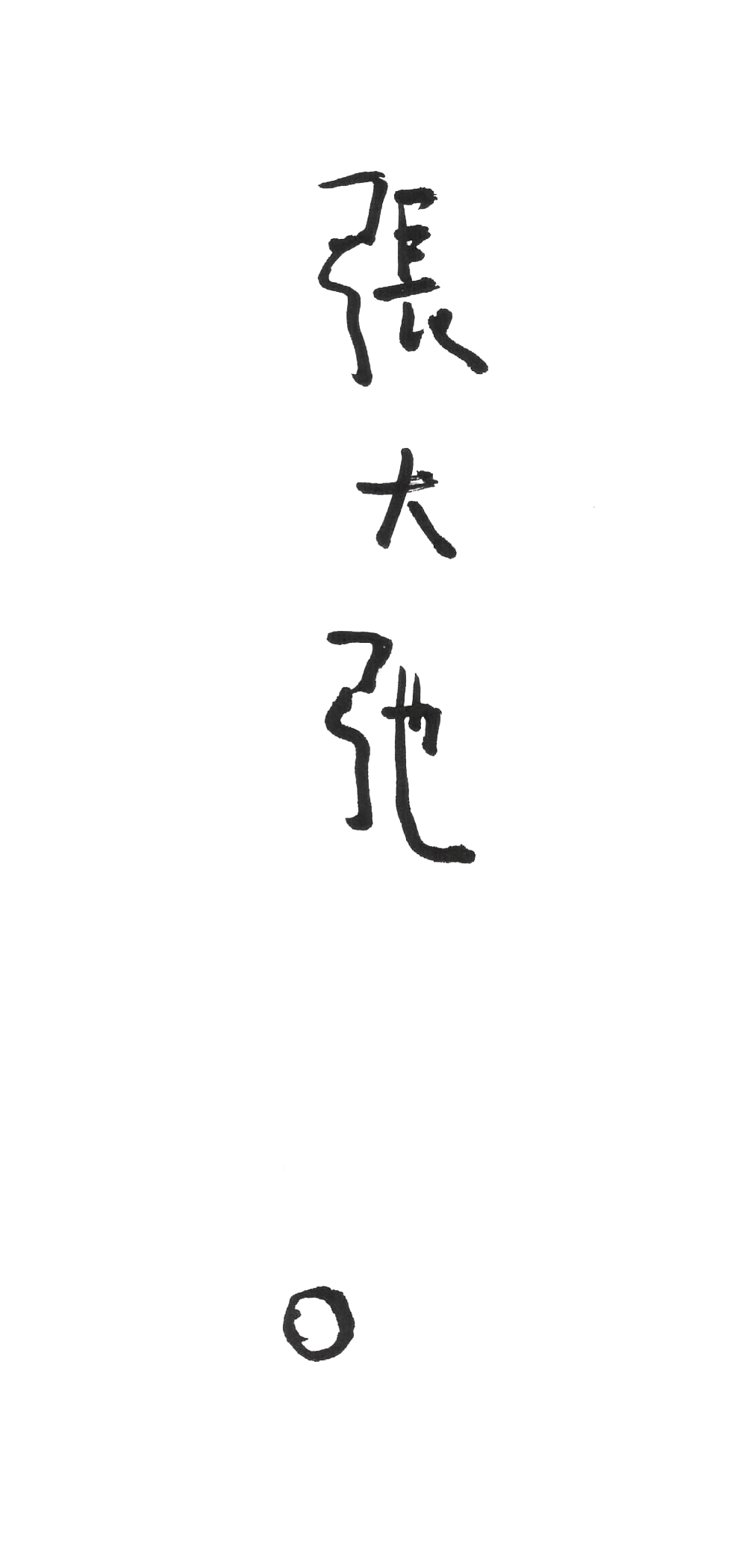/ /
可惜中文动词没有过去时态,我无法在一开始就巧妙的剧透这种“曾经”的预感。反正在出发前,我就有种勉强寻找消失了,或者不确定的美好记忆的感觉。一个是因为明知的政策的不确定,我不知道能走到哪里可能就无法前行了,或者干脆被困。另外就是逐渐强化的人为管理,一定会在视觉和边界上有更明显的表现。但我万万没想到,出发的第二天,在经历了首场雪后,我驾驶的汽车居然把我阻拦在了内蒙的边界线上,历经10多年蹂躏的避震发出了警报,告知我它不行了,无力前行。好在此时我已深入深秋腹地,配合深入咽喉的棉签,我还是可以有一整天来唤醒DNA的权利。描写的深入一些,这里的每株草木,都像我自己的毛发,血脉相连,但又陌生;每座山丘,都像陌生女孩的臀部,可视不可触摸;每个凝视的眼神,都像浴后镜中自己的四目相对;每支奇怪噪音,都像自己房间中发出的异响。来这的目的不再重要,仿佛射精后的空旷和迷茫。但此时你是和谐的,舒适的,沉寂的,自由的。用旋律表达的话,这应当是悲鸣在长空中的小号,漫长而尖锐。曾经认可的那些拘泥于克制的快乐,再不值一提。任何的形式主义,都苍白无力,多此一举。在倒计时有限的时间里,面对自己和周围的环境,时而具象,时而抽象,变成一种短暂存在的方式。
回北京后,弹窗三如约而至。